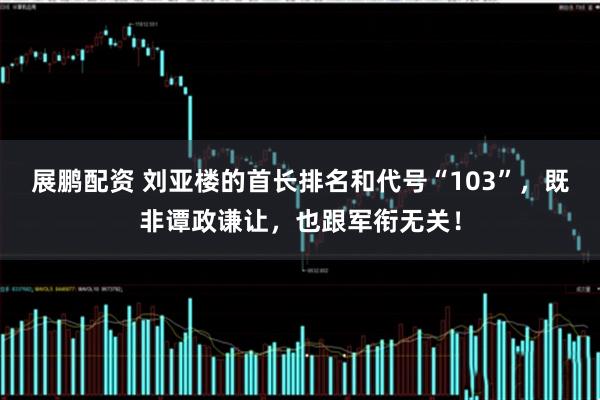
1947年10月展鹏配资,西北野战军彭老总的司令部,在陕北马蹄沟遭敌空袭,所幸是有惊无险;考虑到之前华东野战军司令部,也曾在坦埠遇敌机轰炸,军委严令各野战军领导机关,必须加强保密工作,周副主席还特别要求,各野战军主要军事首长全面启用代号,以防敌监听和侦查!

不久以后,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“东北人民解放军”,重组后的领导机关,认真贯彻了军委的这一指示。当时的东北人民解放军,区分为“东北军区”和“东北野战军”两大部分,但是领导机关暂未拆分,只是首长们的分工有所不同。
其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林总、第一副政委罗帅和参谋长刘亚楼,主要负责前方作战和野战军指挥,战争年代,这显然是头等重要的工作,因此分别启用了101、102、103的“首长代号”,至于其他分管党政以及军区工作的首长,并未使用代号。
也没这个必要,军区工作主要是领导地方部队,以及二线兵团(独立团、独立师)的编训等。至1948年8月间,在确立了辽沈战役的决心之后,根据军委“靠前指挥”的建议,才从军区机关抽调精兵强将,正式组建东北野战军司令部。

“野司”以林总兼司令员、罗帅兼政委、刘亚楼兼任参谋长,也就是之前指挥野战军和作战的三位首长,因此首长代号没有变化,一直沿用了下来,注意野司各首长的职务,都是以“军区首长”的身份兼任的,只是细节稍有变化。
与此同时,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谭政,也兼任了野战军政治部主任,许多历史文章介绍代号为“104”,可惜暂无相关资料佐证,尤为常见的一种说法是:由于谭政将军资历非常深厚,军委给东野电文的抬头,本来都是“林罗谭刘”。
只因个性鲜明的刘参谋长,每每在电报中坚持落款为“林罗刘谭”,如此时间长了,性格宽厚的谭政主任干脆通知有关部门,以后电文中就不要注上他的名字了,于是有了“林罗刘”,好像刘参谋长“争座次”一般,事实果真如此吗?

一、刘亚楼是东野绝对的“三号首长”
战争年代,我军“司令部首长”的排名中,参谋长的座次,必然只在军政主官、副司令员和副政委之后,而在这一点上,东北野战军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,跟同期的其他野战军截然不同。
众所周知,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,是由彭老总“军政一肩挑”,参谋长之上,还有张宗逊和赵寿山两位副司令员;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是陈老总,其下也有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委谭震林。
至于中原野战军,在刘司令和邓政委以下,还有副司令员陈毅、李先念和副政委张际春,因此在这三大野战军中,参谋长都不是“三号首长”,比如中野的前身“晋冀鲁豫野战军”,刚刚成立时的首长名单是:
刘司令员、邓政委、李副司令员、张副政委、李参谋长(徐帅后任军区副司令员),刘邓的首长代号分别是一号、二号,而参谋长李达的代号只能是“五号”,毕竟前面有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呢,建国后二野官兵也都常提起“老五号首长”。

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机关在没有分拆之前,军区司令部统一指挥着百万大军,首长名单是健全而复杂的,既有副司令员也有副政委,排名都在参谋长之前,比如1948年春,军委在关于打长春的回电中,抬头是“林罗高陈李刘谭”。
说明刘亚楼在军区首长名单里的排名,只是第六位,需要指出的是,政治部主任却一定在参谋长之后,注意政治部谭主任的排名是第七!换句话说,即便是在军区机关的排名展鹏配资,刘参谋长也在谭主任之前。
而在单独成立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时,主打一个“精干高效”,没有搞得太复杂,因此只设司令员、政委(由军区副政委兼)、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,并未任命野战军的副司令员、副政委,那么毫无疑问,刘亚楼参谋长就是东北野战军的“三号首长”!

既然是三号首长,那么不仅首长代号一定是103,从此以后,在关于作战的往来电文中,抬头或落款均应为“林罗刘”或者“林罗刘谭”,不可能出现谭前刘后的情况,这是有违军事和历史常识的。
当时作战为第一要务,东野的战役谋划和作战命令,主要由“林罗刘”包办,政治部主任则是在政委的领导下,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,除非重大战役的政治动员令,政治部主任一般也不会在命令上签字。
战时一切从简,因此在军委致东野司令部的日常电文中,抬头写为“林罗刘谭”是极其少见的,更不可能写作“林罗谭刘”!这跟淮海战役期间,军委致华野电文经常性称谓“粟陈张”,是同样的道理。
因此网络上流传关于谭政“谦让座次”的说法,是毫无根据的,无论是军区还是野战军的首长排名,刘参谋长都在谭主任之前,其他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,除非是副政委兼任者,也没有一个排名在参谋长之前!

二、刘亚楼更受林罗首长器重
着重说明一下,谭政从未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的副政委,而是1949年3月以后,在东野整编为四野之后,才正式被任命为野战军副政委,此时四野领导班子已经大调整,不再是“林罗刘”三巨头的格局了。
客观来说,刘亚楼参加革命的时间,确实要略晚于谭政,而且谭政将军在井冈山时期,还曾担任毛主席的首任秘书,但是刘亚楼在红军时期的职务,晋升那是非常迅速的,至长征前夕的1933年底:
在红一军团战斗序列内,红1师师长是李聚奎、政委是谭政;而红2师师长是陈光、政委是刘亚楼,刘、谭皆是红军主力师的政委。刘亚楼赴苏学习之前,曾任抗大教育长,协助林校长的工作,配合更是比较默契。

注意刘亚楼和谭政,都不是东北我军初期的主要首长,而是1946年以后“空降”而来,刘亚楼是在大连与罗政委邂逅,旋被举荐到“东总”任职,林总不仅亲自迎接,还与罗政委联名电请军委,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。
谭政也是1946年从延安到达东北的,而之前东北人民自治军、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部主任,是同样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陈正人同志,直到1946年5月,陈正人调任吉林省委书记,谭政才接手了政治部主任一职,跟刘参谋长的任职时间大致相同。
此时的东北我军,刚刚经历了四平之败,军事形势严重恶化,打仗和打好仗才是重中之重,因此在罗政委没有回国之前,刘亚楼成为林总的主要军事助手,深得倚重和信任,这方面的轶事很多,无需赘述。

东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之后,在司令部建设、部队正规化建设和作战指挥等领域,刘亚楼成为林罗首长不可或缺的首席幕僚长,正式奠定了野战军三号首长的地位,军委和毛主席的作战电文,至此基本写作“林罗刘”。
辽沈战役之后,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,谭政主任亲自起草了《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》的政治命令,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下发各部队,而文件的首长署名顺序正是“林罗刘谭”,这份文件的历史记录,在战史文献中很容易查到。
平津战役期间,刘亚楼更是以参谋长的身份,直接出任天津前线指挥员,统一指挥六个纵队(含炮纵)34万大军的作战,兵力规模远远超过一个兵团,某种意义上,这是按野战军副职来使用的,足见林罗首长的器重!

三、首长排名和军衔没有直接关系
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,是一次资历、功绩和职务的综合考量,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的职务,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,因此不少职务排名靠后的将领,军衔反而要超过这一时期的上级,这是正常现象。
比如二野,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授大将衔,而参谋长李达只是上将军衔;比如一野,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授大将衔、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授上将衔,而参谋长阎揆要仅授中将衔,其中涉及到方方方面的因素。
再比如三野,四个兵团司令员均授上将衔,而参谋长张震也只授了中将衔,这种职务和军衔未必同步的情况,受限于将领参加革命的时间、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职务等等条件,况且在战争年代,我军将领的衔级划分还没有那么清晰。

必须说清楚,军衔那是建国以后授予的,不完全代表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高低,也没有直接联系,张震参谋长代表三野司令部下达的命令,难道四个兵团司令员就不执行了吗?没有这个道理。
四野第一参谋长萧克,授上将衔;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,授上将衔;副政委谭政却授了大将衔,这跟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排名,没有必然的联系,还是那句话,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,只是评衔参考的部分因素。
说到具体原因,一方面是谭政主任,成为了我军政工战线的大将代表;另一方面是刘亚楼参谋长,毕竟基本缺席了抗日战争,期间赴苏学习,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军衔的评定,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

再如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,授少将军衔,而政委陈仁麒为开国中将;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授少将军衔,政委袁升平也是开国中将,难道辽沈战役期间,野司电令要把政委的名字写在前头?
因此,用建国以后的军衔高低,来倒推战争年代的职务排名,是不专业和不严谨的,刘亚楼参谋长作为东野的三号首长,仍然有权给兵团司令员萧劲光、兵团政委黄克诚,下达作战命令,两位也都是开国大将。
东野好几位纵队司令员后来都是开国上将,饶是如此,战场上在电话里听到“雷公爷”的咆哮,他们也得心头一颤,围歼廖兵团时六纵曾一度失联,正是刘亚楼嚷嚷着要“枪毙”纵队司令,“103”那可不是白叫的!

益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